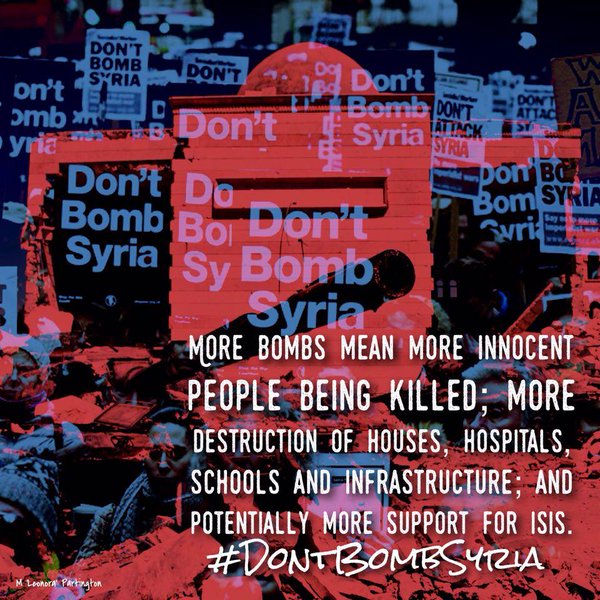文/安然
【一】
《济南回族风情录》里载有一道名菜:蒜爆羊肉,大约还在旧新街的老宅里,西关巷陌犹存时,祖父就讲起过这道菜和另一道叫“塔思密”的神秘佳肴有着某种渊源,这份渊源讲不清理还乱,细若游丝。
可偏有人知其不可而为之,四方云游后,尝尽人间滋味的酸甜苦辣,发现某种味道不仅在某个时刻可以唤醒那些尘埃落定的往事,而且匿藏着有待破译的文化密码和本以为已经消失的隐秘幽微的家族记忆。
过年时,母亲喜欢早早炸下满满一盆焦酥暗红的“萝卜丸子”,她常说这门手艺传自她的祖母——一位身材高大、孀居后在巷口支起油锅卖炸丸子的刚强妇人,我自小就对她的故事充满好奇,后来闲谈中石家庄的大舅舅告诉我,他的祖母是北京通县人,庚子国难(西元1900年)时为避战乱才随家人一路颠簸南下济南,对于口耳相传了一百多年或许早已走样的模糊记忆,我并不敢置信,姑且听之罢了。只是当我起意亲手炸点儿丸子,在好豆网搜索配方,才发现在一堆有关炸丸子的菜谱里只有一份“老北京炸丸子”与母亲的家传做法最为贴近,也是把葱、萝卜切末和面,也是要炸得焦酥暗红。
一种味道印证了一段平民百姓不见于文字的历史。
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曾言:“即使物毁人亡,即使往日的岁月了无痕迹,气息和味道(唯有它们)却在,它们更柔软,却更有生气,更形而上,更恒久,更忠诚,它们就像那些灵魂,有待我们在残存的废墟上去想念,去等候,去盼望,以它们那不可触之的氤氲,不折不挠的支撑起记忆的巨厦。”
很多年后,我尝过了那道京师名菜“它似蜜”,尝过了西域正宗的“卡瓦甫”,在阿帕克霍加墓的巨大穹顶下百感交集地注视过她的棺椁,祖父也故去多年……那酸甜的阿拉伯口味如何来到了西域,又如何进到了清宫大内,很多文化的秘密像一道道沉重的石门向我洞开了,但我,也陷入了更深的世事迷惑中……
我是谁,我究竟来自何方,依旧纠缠着我疲惫的灵魂,神游路上,我依旧不相信生命只是时光中一段孤独无序的存在,我试图向自己证明:人,生来并非只是被打败,并非只是毫无意义的活着……
说起来,我寄生的这方山水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地理里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有倔强的人在这里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以传先王之旧,也有聪明的人调鼎治羹,善和五味。恒公感叹了一句未吃过人肉,“善和五味”的易牙便把自己四岁的稚子做成了一碗汤,“烹子事君”。想来某些人“天上飞的,飞机不吃;地上跑的,汽车不吃;四条腿的,板凳不吃”,而外无所不吃 ,也是其来有自。作为“美食家”的君王最后被自己的厨子和宠臣易牙饿死宫中,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就这样又变回了无权无势的小白……
乏义的饮食与乏义的人一样,是可怕的!
孔子,鲁人也;易牙,齐人也……齐鲁,吾之桑梓之地,父母之邦,生于此间,善恶同处,幸欤不幸?
困厄之时,此思常萦五内——
不做无原则的犬儒,不做现实主义的狗奴才,不做百无禁忌的饕餮之徒……于是便成了心上、舌上时做斗争的教条。
如果说坚持清真饮食也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教条表现,那么,我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
在半岛电视台一期深度报道中,有一句发人深醒的话——在伊斯兰恐惧症患者看来,只有“那些不像穆斯林的人,才是温和的穆斯林”。
如果以这样一种愈来愈离奇的尺度衡量,我就谢绝这个“光荣的称号”,不做那些有色镜片后面的那个“温和的穆斯林”。那些以反恐为名的刀笔吏已偏离了理性的思考,循着强盗的逻辑一路暴走而去,对这个渐渐远去的世界,夫复何言。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无法释怀的,不仅在心上,也在舌上!无论在心上还是舌上都持守一种千年不变的道义,即使为此付岀做人纠结,乃至失败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已是一条不再退却的底线。
因为有时舌尖上的清真,便是心尖上的清真。
【二】
如同佛寺、道观,既然清真寺以“清真”名之,“清真”的题中之义,应是不言自明!
回溯历史,“清真”一词是和“朵斯提”(Dasti 朋友)、“索哈伯”(Sahab 圣门弟子)、“舍西德”(Shehid 牺牲)、伊玛目(Imam 领拜人)、主麻(Jumma 聚礼)、衣扎布(Ijab 婚约)、穆民(Mumin 归信)、穆斯林(Muslim 顺从者)、阿訇(Akhund 教长)、邦达(Bang 宣礼)、沙目(Sham 昏礼)等大量汉语穆斯林辞汇一道在明代的回族先民中间涌现的,其中有阿拉伯语,也有波斯语、突厥语,折射出当时回回人来源和构成的多样性。唐宋来华定居的阿拉伯、波斯“蕃客”,说阿拉伯语、波斯语,而元初东迁的大批“西域回回”则多是操突厥语的各族人。明朝政府强制穆斯林说汉语,本为加以同化,但由此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在语言庞杂的回回人中间形成了统一的易于沟通的共同语言,这是一个民族诞生的必要条件(参见邱树森《中国回族史》,“回回”共同语言的形成)。
在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宗教辞典》一书中,更是把“清真”一词在中国伊斯兰教徒中广泛使用的时间精准定位到了明弘治、正德(1488-1521)年间。明末清初的回儒们在其著述中以“清净无染”、“真乃独一”、“至清至真”、“真主之清净”、“真主原有独尊,谓之清真”来描述、称颂独一无二的神——安拉(Allah),为“清真”一语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内涵,“清真”遂长期作为伊斯兰教(Islam)在汉语语境中的指代而存在,故有“清真教”、“清真寺”、“清真言”之说。
在今天的“维基百科”上,将“清真”与阿拉伯语“合法的”一词的拉丁字母转写Halal相对应,其实,最初“清真”一词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在汉语语境里与Islam相对应,“清真”只与食物相关是一件非常后现代的事儿。
语义随着时代和中外文化交流发生了变迁,但“清真”一词的涵义仍未脱离伊斯兰教的阐释范畴。
清真—Halal既为“合法”之义,那么,合法性又来自哪里?
很久之前便听过一个民谚,叫“三品以上必反教”,我曾向祖父追问缘故,他讲三品以上的大员便有机会觐见皇帝,觐见之后必会赐宴,在皇帝老子的御宴上怎能推却那份入口的猪肉呢?
“吃猪肉出教”的思想在回民的传统里可谓根深蒂固,吃猪肉被俗称为“坏口”,于是,一口猪肉便成了一些人心中合法与非法、在教与出教的那条界限。这固然反映了民众对本民族信仰的珍视,对宗教纯洁性近于苛刻的捍卫,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于宗教本质的一种误读。
饮食关乎信仰,却不能框定信仰,一种宗教信仰又岂能由吃什么来决定,信仰是心灵的渴求,只取决于心灵。
正本清源,伊斯兰教并非一种苛刻的宗教,真主的两大属性是“仁慈”与“怜悯”,真主曾说:
“(助迈尔章) 39:53 - 我的過份自害的眾僕呀!你們不要絕望,我必定要赦宥一切罪過,以至赦的至慈之名。”
而关于饮食,《古兰经》同样既给出限定又给出宽恩:
“(巴格勒章) 2:173 - 他只禁戒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凡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份的人,(虽吃禁物),毫无罪过。真主是至赦的,至慈的。”
苛刻的是无知的人,非是化育万物而无所求的神。
【三】
但从另一方面说,千百年来的饮食禁忌确已化入一个民族的底层意识,甚至成为一种生理反应。
四年前,当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引发万人空巷的收视狂潮,风靡大江南北之时,我却对之兴味阑珊,甚至不停摆弄着手中的遥控器,第一集里用咸猪肉、冬笋炒制的“腌笃鲜”和诺邓火腿繁复详尽的制作过程即已让我避之唯恐不及,只得有所选择地去看一眼。禁忌即如是这般,已成好恶,不由人也。
由于回民是世居中国的地理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长期的比邻而居,令大多数中国人对回民的饮食习惯并不陌生。
由回民的饮食习惯延生出的清真餐饮业自古有之,这一行当不仅方便了教内人,也深受到教外人的喜爱。“燕园三老”之一的张中行先生在他所写的散文集《负暄琐话》里就有一篇《东来顺》,他起笔便说要为一位进京的回族友人洗尘,“地点当然最好是东来顺了。”
不仅如此,他还述说起自己在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当穷学生时与东来顺的老因缘。听他讲坐在老东来顺门内的穿长袍的二掌柜如何谦恭迎客,跑堂的伙计如何殷勤待客,对自家的饭菜又如何如数家珍,食物是如何的物美价廉,“比如说,衣袋里只剩两角钱,那也可以走进去,吃二十个饺子,喝一碗粥,总共九分钱,大大方方给一角,听一声‘谢’,走出,到丹桂商场,选一角钱的旧书一本,高高兴兴地走回学校。”在一个礼乐崩坏、人心畸变的颓世里,这样温热的讲述也自是令人向往。
我注意到,在文中张先生先后有两处提及“他丝蜜”( “他丝蜜”应就是“塔斯密”或“它似蜜”的转写),敢情他老人家也是一位爱吃羊肉爱吃甜的主儿。说起羊肉,有人会担心膻腥之味,可吃“它似蜜”全然不必有此担心,尽可忘怀于它的甜蜜里,同时这道在“南甜北咸”的口味分布中殊异的酸甜又是一种暗示。
围绕着“它似蜜”这一道菜,民间流传着两个典故。
第一个故事便与我在喀什噶尔探望过的那个魂归故里的女人有关——
大清乾隆年间,随香妃入宫,一批来自西域的厨师也一同进了宫。有一回,乾隆皇帝乘兴吃了回“塔斯密”,不禁龙颜大悦,询及香妃此菜何名,答曰“塔斯密”,乾隆感其甜腻异常,入口滑嫩,如同稠蜜,但名不“雅驯”,故而赐名“它似蜜”。
这是一说。
另一说是,晚清时慈禧太后在宫中用膳,一道色泽红棕、肉质软嫩的菜上来,老佛爷尝后十分喜欢,问:“此菜何名?”因是首创,制作这道菜的回族御厨一时答不上来,遂灵机一动,答道:“请太后赐名。”慈禧随口说道:“此菜如此甜蜜,就叫它‘它似蜜’吧”。从此“它似蜜”这道菜流传至今。
这两个典故略有差异,却无一例外地指出“它似蜜”最初是一道宫廷菜,而且与穆斯林渊源甚深。
两个典故到底孰真孰假,其实,在我看来都是半真半假。
西域菜乃至更西一点儿的阿拉伯菜在口味上都以辣、甜、咸、酸著称,文明在那一片广阔相连的地理空间中不仅在宗教上、人种上、语言文字上、音乐舞蹈、诗歌传说……甚至饮食上都有着相似性。甜蜜异常的“它似蜜”保留了西域菜的特点。
同时,“它似蜜”的烹调过程则又是使用的中原技艺——“爆炒”法。在清初即扬名海内的四大风味菜系中(鲁、川、粤、淮扬),尤以鲁菜的“爆”“塌”更有独到之处。乾隆朝以“性灵说”主盟诗坛的袁枚也是一位美食家,他在 《随园食单》就曾以“滚油炮(爆)炒,加料起锅,以极脆为佳”来形容济南的爆炒菜肴。
去岁居京期间,听闻一说,老年间的京城勤行里山东人居多。回族烹饪大师、北京又一顺饭庄主理厨政的杨国桐先生也在其主编的《清真菜谱》一书中说,北京地区的清真菜深受山东、淮扬菜的影响。
于是,如此看来“它似蜜”仍是融合之物。也不妨如此申而论之,“融合”不意味着抹杀个性,抹杀个性不是融合,而是同化,融合是取百家之长补己之短,是文明间的彼此欣赏、和而不同。如此,这个世界才能和平,才不恐怖。当然,那些刑名法家之徒是不会反躬自省的,动荡是其利益所在,一个和平的世界在他们的冷眼看来太过理想化太不真实了吧?
太甜蜜的东西大概是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虚幻感,于是,改制而来的“蒜爆羊肉”为了适应现实降低了菜品的甜度,提升了北方人喜爱的咸度,并以蒜米调味,增添一种微辣的感觉,按照某些人的观点来说是进一步地中国化了。
“蒜爆羊肉”曾一度是济南穆斯林的一道招牌菜,据说在萧弊的七十年代,擅长烹制此菜的清真饭庄一天尚能卖出五六十份,彼时物价也低,一份五角钱的蒜爆羊肉加一份一角钱的羊肉水饺便能让来打牙祭的食客满意而归。一道出自名厨之手的“蒜爆羊肉”盛在白瓷盘中如一块油亮的琥珀,如今这样精良的制作却已难觅踪迹,今日济南的清真餐饮业水平参差不齐,诚不足道哉。
【四】
记得少年时,曾翻过一本小册子《孔子传》,对其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微管子,吾披发左衽矣!
“披发”不难理解,满大街都是披肩发。但“左衽”又是怎样一种奇装异服,以致孔圣人要如此排斥呢?这个问题藏在我心里很多年。直到终于弄明白所谓“左衽”“右衽”不过是衣襟向左掩、向右掩的区别,还是不解“右衽”是否真的比“左衽”要高明,以致夫子如此地在意与坚持?
小时候辞旧迎新,一大家子总要守在祖父身边,而年夜饭上“吃锅子”是不变的成例。所谓的“锅子”,就是一只铜皮火锅里塞进了满满一锅的各种炸货,再浇上牛肉汤汁,渐渐地,当红热的木炭开始从烟囱里喷溅出火星,堂屋的那张八仙桌上也就飘荡起香气四溢的热气。
据说这样的传统启自我的三位太爷爷——崔德、崔聚、崔兴——兄弟三人幼时失怙,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开始,硬是白手起家,创办了享誉西关的“德聚”字号。
(三老爷爷晚年的留影)
曾祖兄弟三人秉性不同,各有所长,长兄崔德为人聪慧,机谋善断,二哥崔聚忠厚沉毅,三弟崔兴一杆长枪威名赫赫。家族中兴后,曾祖们注重在文化上教养子弟,祖父辈中有多人在当时的新学“正谊中学”就读。
已拆去的北大槐树清真寺的大殿上有崔德代表家族捐赠的三根木梁,寺内碑刻有记;崔兴曾为民国时期清真北大寺理事会的理事,至今仍有人撰文回忆……曾祖父们是笃行清真教门之人,就如除夕夜选择火锅而非饺子——这一象征意味浓郁的符号化食品,也是出于他们在信仰上的朴素意识。
圣人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曾说:谁效仿哪个民族的习俗,他就属于哪个民族。
我的太爷爷则用一段大白话做了自己的诠释:“人家过年,咱总不能从年初一跳到年初二吧?人家吃水饺,咱吃火锅!”
多年后我回味家族往事,发觉我的祖先也是在意“左衽”之人,他们也有自己的人生哲学——“经权之道”。他们竭力维护的那心尖上的小事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陌生的异域信仰,也是人所共有的一种情感、一份尊严与一脉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