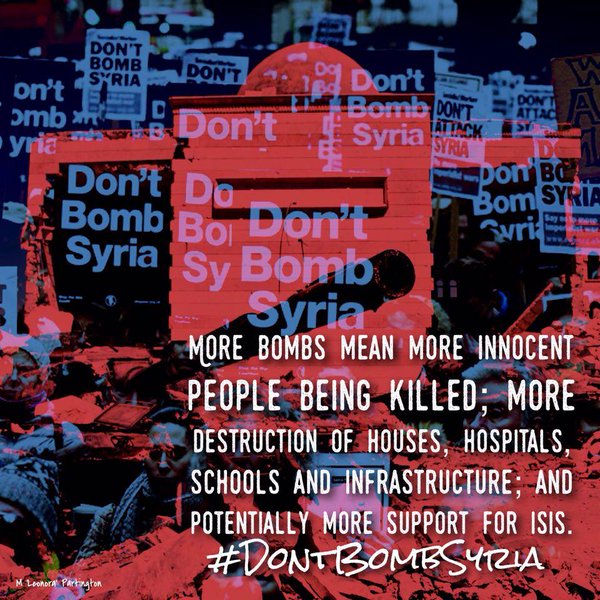安然/文
对参与75事件的维吾尔民众的审判,效率极高——往往当天开庭,次日即行宣判(有几起案件甚至是在一日之内完成从开庭到宣判的全过程)。再经由官方媒体配合报道,整个过程被渲染得俨如一场简单而隆重的政治秀。如此匆匆走过场,实不出意外。因为中国官方从一开始就将西元2009年7月5日那座疑云密布的乌鲁木齐——发生了一场很快夭折的维吾尔大学生组织的抗议韶关种族仇杀的游行和随后异军突起的汉维街头械斗——断定为少数民族分离运动精心选定的暴乱地,卷入事件的维吾尔人在代表主流群体“汉民族”利益的当局口中是未审先判的“暴徒”,他们是挑战“大汉王朝”大一统敏感神经的国家公敌。

有“消息灵通人士”在维吾尔在线国际中文论坛得意洋洋地宣称,整个审判中将有100人被判死刑。由于这些人之前放出过只有新疆安全部门才掌握的75当日的市政监控录像,在以往的论坛发言中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新疆汉人”身份……因此,他们此刻的再度爆料,令人感觉格外意味深长。关注维吾尔命运的人们急于知道是什么样的背后原因和现场具体诱因引发了暴力,如果法庭在审判中不周详地考察这些因素,就如那些“新疆汉人”所愿地大开杀戒,难免被外界贬斥为充当了种族清算的并不体面的遮羞布。事态如此发展下去,审判“75”充其量只能起到对主流群体的民愤有所交代的作用,除此而外,不仅距社会正义愈加遥远,而且必将加深已有的民族裂痕。
司法审判的最基本的准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然而,新疆的事情向来最具“神秘感”。即以对75事件的描述为例,当事双方就各执一词。当局一方继续沿用对少数民族抗争活动的定性,用“暴乱说”一言以蔽之,并在宣传中反复强调作为原住民的维吾尔人对汉族移民进行了暴力攻击;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组织的指控中则有“灯黑后枪声大作、有上万人一夜之间不知所踪”等情节。虽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女士和众多非政府组织要求就新疆事件展开公开的国际调查,但都遭到中方断然拒绝。中国政府回绝皮莱女士的话算是很客气了,称之为“过分关心”。
外人不准关心,内部则乏同情者。邓玉娇杀人能赢得全国上下一片喝彩声,一方面她自有可悯之处,另一方面她本人并非维吾尔那样在种族、文化上与汉人差异巨大的异域民族的成员。人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少数民族的暴力时只有不解和愤怒,但之后又不愿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做全面的了解,更无意去体会少数民族积聚已久的对族群安全的焦虑,而这恰是民族动荡的主因。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家实力的增强非但未带给中国的主流群体“汉民族”以安全感,反而促其加快了削弱少数民族在经济发展、教育、语言方面自治权力的进程。在迫使一个民族在政治上从属于另一个民族之后,开始谋求令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也归并入主流群体之中,中国境内所有真实存在着的少数民族都真切地感受到了此种文化生存上的威胁。
60年来,中国陆续以军垦、支边、开发的名义对新疆这块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大规模殖民,当地汉族人口由1949年的1%猛增至如今的40%以上,在首府乌鲁木齐汉族人更是占到人口比例的80%,令少数民族在传统领地上已然成为少数。
在汉语已获得官方语言的地位后,为进一步压缩维吾尔语的使用空间,当局强制少数民族从小学习、使用汉语,誓将一个语言群体连根拔起。
维吾尔民族和回族一样信奉伊斯兰教,其宗教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核心部分。深味于此点认识的汉族殖民当局对宗教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压,使尽浑身解数。为了限制乃至最终消除伊斯兰教在少数民族内部的影响力,当局严禁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最近更表态要将“诱使未成年人信仰宗教”列为非法。这些明显具有针对性和歧视性的地方法规的制定首先就违背了中国宪法对公民信仰权利的公开承诺。一个人自是生在中国,即是中国的公民。无论其年龄长幼、民族不同,都应享有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利,包括信仰权。身为少数民族的父母对子女教育引导的权力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难道少数民族传承本民族宗教信仰、文化形态的努力在中国都属于非法活动,难道新疆当局的所作所为可以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无法无天?!

当少数群体被弱化至丧失区域性人口优势或其区域聚居规模不足以维持其语言时,它即丧失了地方自治的能力,在文化上等同于消亡。这就是中国少数民族面临的残酷现实。但每当这些族裔文化群体向政府要求自己的集体权利时,都会被加之以分裂的重罪,倍遭摧折。而少数民族都很清楚维持殖民体系运作和充任镇压机器者正是当地的殖民群体,这就是无论是拉萨还是乌市的反抗者为何都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当地的汉人的原因所在。
一味地将人们的视线转向对暴力的谴责,而对族裔文化公正采取漠视态度,既不公正又十分虚伪。
当主流群体对国外势力单方面改变其疆界、体制或自治权的企图进行暴力反抗时,这样的暴力被称为集体自卫权利;为什么少数民族就不可以为保卫自己的传统领地、文化和自治传统而行使集体暴力?
面对棘手的少数民族问题,有一种解决理论在民主成为共识的时代浮上水面:即主流群体成员通常愿意劝说少数民族优先考虑民主和人权,而不是他们的少数群体权利问题,这种做法并非出于偶然。因为主流群体成员明白少数群体权利问题向后推迟的时间越长,主流群体得到的时间就越多。他们可以侵占更多少数群体的土地,削弱其教育和政治体制,直到少数民族再也无力作为一个有活力的文化个体存在下去并实行有效自治。
我不认为中国的那些拥有悠久传统和文化的少数民族会在压力下失去生存的智慧与机会,蛮横的镇压绝不是中国民族问题的保命金丹,逐步推动人们正视族裔文化公正才是惟一可行也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