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当局已对另一种极端采取行动,我也准备向“宗教极端”开一枪。对于“清真泛化”背后的那种偏执,那种以Haram之名对人们生活的干涉,我早有领教,多年前,我就亲眼目睹过这种不近人情的偏执,还曾以小说之名记下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经历……
-----------------------------------------------------------------------------------------------------------------------------------------------------------------
分割线
小说: 终究意难平【2016修订版】
文/安然
“介廉种子,官川开花,我来结果。”彼我非我,我说不出如此雄心勃勃的偈语。自落生起,我就脱离了民族的母体,我长不到那棵果树上去了。我知道,自己只是借住在人家果园中的一个过客吧,来静观一季从花到果的风景。
主人“体恤”我翻山越岭之苦,嘱我再休息、适应一段,这样,才开讲没几日的汉语文课便戛然而止了。
这座古城不大,坐落在一片盆地之中,当地人将这样的山间平地称为“坝子”。与炽热难耐的北国相比,这个地方凉爽多雨,有一次走在街面上竟目睹了晴雨两重天的景象,西边是一轮老阳依依惜别,东边却在一块乌云笼罩下阴雨霏霏。更多时候,我足不出户,古寺西楼那间门不常开、帘幕低垂的斗室就成了我的“退隐之地”,我在那里面望乡、感伤、青灯古卷,过着就差一身僧衣的方外生活。
当然,吃饭还是要到楼下的食堂走一遭儿的。那日中午去的太早,有米无菜,只盛了半碗白米饭,即欲躲回小楼成一统。上楼时遇着两个女生正一人一边拽着一根绳儿晃悠悠地提着一件装杂物用的纸箱在台阶上往下慢慢蹭,见不得女人为难,不及细想就向前替过她们。那箱子单臂一提便觉沉重,真不知两个长袍曳地的小人儿是花了怎样的气力从四楼上把这个大家伙弄下来的。
顶楼的那处神秘的女生部在如这座高原山城清晨的烟岚般静悄悄地消散。因为古寺面临拆迁,这几日就要让她们先期搬去郊外的临时校舍。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心中发问,为什么不让这些女生去东边的那座崭新的白色大寺借读,只隔了一条街嘛,徒步就到了。这个地方的大小寺坊都修有自己的教学楼,却常常空置,少有统筹,各忙各的天地……思路一牵涉到回族内部的那点事儿啊,就变得暧昧纠缠,没法想下去。
帮完那两个女孩,回到自己的房间,吃饭、洗刷,一切收拾停当,闲坐中又想起她们。
是否有更多的女生行李在往下搬,自己是否应该走出去看一看,而你的多情行为又是否会冒犯教门中古老的封建传统?
课堂上,学生的轻慢之色尚历历在目,还在反省课堂上是否说了过头话,刚刚暗味过热情热心换来冷淡冷漠的人生,才寂寞多久啊。
可你不是一个只在意自己的爱憎、从来我行我素的人吗?以前,你不是一个将女人的苦难视作红尘中最不可饶恕、最不可忍受之事的人吗?在良心与物议之间,你竟没有了抉择?
内心不再争辩,推门而出。这时,楼道上下早已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行李,女人的东西真多啊。一边心里暗暗叫苦,一边开始一件件地把东西往楼下运。
从寺门口到停着大巴车的主干道,中间还有一段短巷长街的石板路要走。有些女生就站在行李堆旁无助地向北边的巷口呆望着,那窄窄的巷口被沿街一色的木制旧屋围得只剩下一片巴掌大小的光亮,暗红色的散发着陈年霉味的小巷一直延伸到那个尽头。
一人之力肯定不行,我想起要喊几个男生来帮忙,他们正在不远处的二楼大厅里热火朝天地打着乒乓球。
“你们怎么不去帮帮那些女生,让她们自己搬那么沉的东西?”我闯入大厅,对男生的麻木感到不解,他们的情感里难道不懂得怜香惜玉?
“学校就让她们自己搬,不让男生帮忙……”那些男生大概被我这个新来的另类“老师”震惊了,纷纷停下手中的球拍,一脸错愕地望向我,直到人群里有人小声嘟囔出了“原由”。
“学校?!”我也震惊了,怎么会是“学校”,学校为什么会阻止同学间的互助友爱?!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规定,我不信:“这是谁说的?”
人群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马主任!”
有人躲在别人身后喊出了答案,这个名字让我心里咯噔一下,一时无语。
虽然初来乍到,一切还不明就里,但我也隐隐觉察着这座小院内的“校园政治”;虽然这里被人们称作“真主的天房”,被视作“净土”,但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世俗的力量还在强烈地左右着人的生活,我有太多的不理解……我不理解为什么人与人、心与心之间依然疏隔;我不理解为什么人们更看重那些墨守的与现代进程背道而驰的陈规,而非向内心深处挖掘的灵修;我不理解不平等与贫富差距在这处“净土”内依旧处处可见,并且,在一种教会学说的包装下变得合法化,这样的意识形态才最让我不能容忍,因为它亵渎了我的理想。
我暗地里从学生口中听到过各种各样的“规定”,其中那些以宗教之名的规定开始摇撼我的信念——一群刚入学、稚气未脱的一年级女生悄悄跑到我的房子里七嘴八舌地说给我听,她们的老师告诫她们——女人的声音是“羞体”!我和她们一样感到匪夷所思……站在那间明亮的大厅里,我忽然想起了这句话,仿佛有些明白了,在男生与女生之间垂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帷幕……在这个败落的即将被拆迁的院落里,它给我呈现的民族景象和信仰表现同样惨不忍睹,以致我时时怀疑此行实乃阴谋之旅。
“不管他!有什么事让他来找我!”积聚在心头的沉郁在那一刻爆发了,我像一个煽动者一样向男生们呼吁“造反”!
那些男生还是太年轻,他们竟然被我——一个无权无势的新老师——打动了,于是,他们跟我走了,众人合力总算是将一地行李送到了巷口。
前方是一列送人的车队,女孩们则被路口熙熙攘攘的人流隔在了这一边。酷阳下,她们头顶的丝巾闪耀着一片异彩,在古寺之外的世界里略显张扬。这永不摘下的向有争议的覆盖啊,此时似是由柔弱的女人扛起的一面旗。这是一面挡不住灼人的热浪也阻挡不了他人锐利目光的旗啊,忍受是为宗教,可在这么漫长的人世间你要忍受多少孽障才能守住你的信仰?这裹到眉毛的印花头巾,这头巾下的晶莹的大眼睛……我先是站到路边的一条石凳上痴痴地凝望着眼前的青春烂漫的生命,内心忽然就像是被什么飞来的东西击中了,有些痛有些闷。后来终于在路边的一小片树荫里颓然坐下,泪水无端地盈满了眼眶。
泪眼婆娑中,脑海里又蓦然闯入了那片白色的建筑,我仿佛又是在古城的迷途中意外地目睹了这一切:纯白色的大寺、纯白色的烈士坊,石剑一样直指长空的纪念碑,还有那口由纯白色的大理石重新砌好的烈士井。沉默的建筑群仿如披着一身让人肃然的缟素,静静等候,我惊呆了。
初见那块记录着“咸同屠回”历史的石碑时,心头曾掠过须臾的绞痛。
“屠杀伊始,有近千回民仓皇逃进南寺以求避过凶锋,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团练头目穷追至寺,先残酷屠戮后放火烧寺,置逃难者于火海。妇女为免遭凌辱,纷纷投井殉难,此即烈士井之由来也。上世纪中叶,后人两次从井中尚淘出骸骨近十牛车,含泪安葬于碑天公墓。”
暗夜里,古寺深深,惟有寂寞。拿出白天手抄的那片文字,誊入笔记,心却已如枯井。
我所执教的这所古寺中的经学生,让自己对回族的想象从云端降到了谷底。这些来自乡村的子弟多有初中辍学、混迹社会的经历,以他们那点可怜的文化基础却要被雕凿成教门的栋梁,自己的心灰意冷是前所未有的。
南北西东的游历,慕名寻访着传说中的“回族的故乡”。天涯羁旅中,尽管彼处都涂上了一抹份属回族的白色的乡愁,就如这座古城,放眼望去,回民的馆子、衣饰、望月塔是它最独异的景致,但它们皆非真境的花园,距梦中的“古丽斯坦”还很遥远。
即使灯残梦灭,可作为一个回族人,终究意难平啊。
泪水肯定是在那蓄积已久的情感催动下,突然而至。只是坐在这行人如织的街头,一时间我自己也无法一下子道出:我到底是为谁又是为何?
是因为我生平第一次目击了这么多美丽的回族少女,她们身上与生俱来的母性魅力再次唤起了我对精神归乡的美好向往?还是她们和一百五十年前的那些投井的如花生命之间在民族身份与精神谱系上的一致性,让我在孱弱的民族现实中感受到了一阵来自深渊的寒意?如果是前者,我是为自己的“永远的异乡人”身份在哭泣;如果是后者,那么我还是在为生身的这个民族而哭泣。抑或,两者之间在很久之前就连缀成一体了。
在这块曾经发生过巨大悲剧的土地上,历史在被人群所淡忘。甚至那些我为之掬泪的少女也未必知道或在意自己求学的这块土地上的往事。“往事如烟”是国人习用的修辞,也是这个社会的现实。
在西方,自二战之后人文知识分子就一直通过哲学、神学和各种文艺形式,沉痛地反思奥斯维辛的罪恶和不幸。那不仅是曾经遭受屠杀的犹太人的不幸,它还是西方人的乃至整个人类的不幸。这样恐怖的大屠杀是由人类自己完成的,如果不反思,它会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群中重演。奥斯维辛不仅是纳粹之恶,它同时也是人性之恶,正如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所指出的那样,德国人对纳粹暴行负有集体责任。
很遗憾,人类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对历史的认识从未达到过这样的哲学高度。“咸同屠回”没有像“奥斯维辛以后”[After Auschwitz]一样在哲学著作中成为一个醒目的术语,反而在眼下的史论中渐渐演变成语义不明的一段。
当我陷入纠葛的内心世界时,是一连串清越如铃的女声——那“不清真”(Haram)的声音——将我唤醒。“谢谢你,大哥!”女生大都已上车,一个女孩从窗口处探着身子向这边挥手,她的脸孔上泛着一种光辉,绸缎一样的光辉。光辉的底子是稚嫩、真诚的羞涩,淡淡的红。我很久没有看到了。她们不知道我内心的脆弱与忧伤,我努力展现着“大哥”的风度。
直到车开走了,我还在那片树荫下悲伤不已。
2010年8月于**
2016年再次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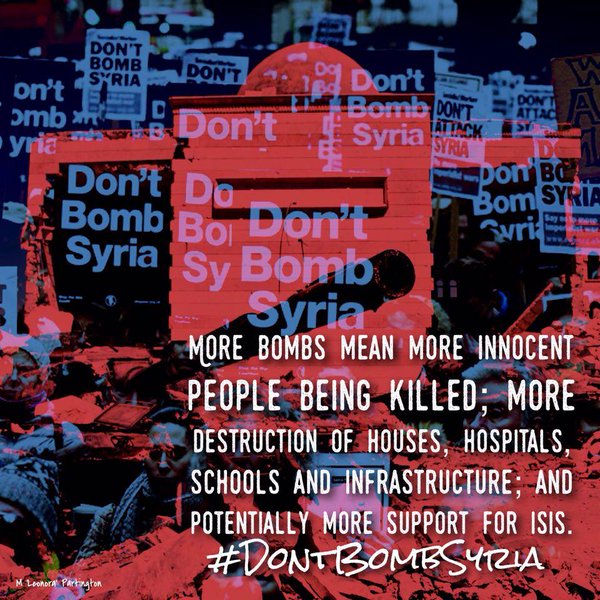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